中国当下的精神危机与
思想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课题。思想建设之于中国现实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在于,思想建设是解决中国人当下精神危机的唯一方法。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特点。现在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没有宗教,只有现代宗教与原始宗教之分。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瞿同祖:)。三千年前,中国从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原始宗教式微,逐渐消失。国家的管理即处于一种理性的指导之下。因此,春秋时的孔子,从来不说“怪力乱神”,甚至不言“性命与天道”。儒、墨、道、法诸家皆没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崇信佛法(梁武帝),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宗教。而佛教、道教,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家宗教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在当今国际和国内局势风谲云诡、极为复杂的情形下,中国的这个传统,对于避免宗教冲突,减少国际对抗,实现和平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积极的因素。但是,由于没有宗教的传统,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却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释、道为内核的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支配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要资源。正因为如此,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获得一种平衡发展,人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具有相应的目标,这两方面的需求能够得到一定的满足。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原有的传统儒释道思想资源,肯定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因为,我们面对的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仅仅凭借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不能满足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因此,必须有新的思想创造,来回答当下人们提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缺失,就是这种直接切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新的思想。
思想缺失,对于个体是失去灵魂,对于国家是失去国魂。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实际上也是痛苦的人生;没有国魂的国家,是虚弱的,外强中干,不可能强大。简单说,没有思想就没有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的河流中,思想问题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源头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把精神生活过度清教化,思想与主义一体,“狠斗私字一闪念”。80年代以后,我们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上又放任自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根源在思想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问题,一个好坏问题,根源上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可以说涉及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是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我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正是生活在信念破产的时期,他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决定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与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不同,是独特的文化和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与几千年的传统决裂,因此,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也是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道路。
首先,从国家的政体和理念来说,当今欧美的政府,职能非常有限,没有管理国民的精神生活的职责和权限。它的这些职能是由教会承担的。人们的精神生活要求,一般也不会向政府提出。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把这些要求完全切割出来。因为,中国没有国家宗教。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体制,由此建立的系统的文官制度,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历史意识惯性,与西方的国家理念相距甚远。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是短暂的,国家不统一,是知识分子的一块心病。陆游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而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没有统一,美国也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基本没有。印度与巴基斯坦原属同一民族,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成为两个敌对国家,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当今的中国人既有自由平等的要求,也有孝敬父母以及家族血亲的观念。从中国人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甚至很多贪官受贿,多半也是为子女着想。至于已经发财致富的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子女问题,而没有子女,或没有男孩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一般把家庭、家族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个人的利益,与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思想差距很大。这些问题用西方的观念,包括基督教的观念都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中国的国家体制、法治思想、政治观念,都不能从西方照搬,也不能从中国古代直接获取,必须有新的创造,需要整合西方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创造。而制度、观念创造的前提,就是思想创造。
由于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社会风俗习惯与西方社会的不同,当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建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体制。从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方人的精神追求密切相关,无论是马克思说的追求财富的贪婪,还是韦伯说的新教的精神,这些与中国人“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和气生财”的理念都很不相同。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贩卖黑奴这样的罪恶历史(现在出现的拐卖妇女儿童事件正是背离传统,值得我们深思)。现在西方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问题,也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有巨大的差异。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生活在传统与文化之中的。例如,中国人的家族观念、裙带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就会有巨大影响,包括负面的影响。而且,马克思、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西方社会体制,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它的顽症。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崩盘,震荡的烈度与深度越大。2008年金融海啸的出现,让所有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世界未来的经济问题仍然是个巨大的谜团和困惑。因此,仅仅跟在西方经济学家后面鹦鹉学舌,不仅不能回答世界经济问题,更不能回答中国的经济问题。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深刻思考民族思想深处的观念,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必要的前提。而这一切,也需要真正的理论创造。经济学的理论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谁也不能否认,、是真正的新思想的创造。
此外,还有科学的创造、发展问题。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说过,中国至今还没有自然科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只是停留在模仿西方科学的阶段,而俄罗斯是有科学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也是一种思想的创造。
科学源于对世界本源的探讨,对于真理的追求。因此,西方最高的博士学位,叫Ph.D,即哲学博士,道理也在这里。中国目前狭隘的科学追求其实是模仿。例如简单否定中医,就是出于对科学本身的不了解。中国的科学发展如果没有自己的道路,就不可能走出模仿别人的窠臼。模仿别人永远达不到科学的最前沿,即使到达了,也不会往下走。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照搬西方的思想和观念,既不能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建设。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思想的创造。一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源于思想的创造。
如何实现思想的创造?
思想创造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极为重要。同时,思想创造也是非常困难之事。因为,思想是炒作不出来的,模仿不出来的,金钱买不来的,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专利。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帝王、君主让自己承担思想家的职责,甚至基督教的教皇也没有这样做。思想创造与科学创造一样,是人类在智力上的奥林匹克比拼。科学创造实质上就是思想的创造。
因此,思想的创造不能指望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没有这个职责。也不能指望职业商人和社会其他从业人员。
在古代希腊,自由的奴隶主具有创造思想的可能。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基本上是一些以思考为职业的人,如孔子、孟子、荀子等,董仲舒曾经“三年不窥园”,才有“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和“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
现代大学出现以后,思想的创造基本上都出现在大学。因为,大学里有一批以思想为职业的人。他们无论是智力、知识以及志趣,都具备了思想创造的条件。但必须让他们自由创造,而不是按照指令批量生产。因此,政府对于大学的思想者给予了特别的尊重,尊重他们的思想创造,不干涉他们的思想创造。即使是有些思想与政府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水火不容,政府也不加以干涉。马克思应该算一个例子,虽然他不在大学。
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思想是体,宣传是用。没有思想,就无法宣传。没有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品。因此,思想家不是宣传官员。思想建设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不能让思想家写宣传小册子、政论文,当审查文艺作品的审查官,书报制度的检察官。
思想家有思想家的职责。例如美国的亨廷顿,他不是总统助理,也不是国务卿,他只是个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亨廷顿对于美国的国家政策的影响,是任何官员所无法代替的。现在美国把对于伊斯兰世界敌对势力的打压放在第一位,这个政策超越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藩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亨廷顿的影子。
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而思想创造的最大可能是来自大学。严格地说,思想创造是产生于真正的大学。如果政府把大学变成一个行政机构,大学的教授都把成为官员当做人生的追求目标,这样的“大学”与思想创造绝对无缘。现在虽然每年中国大学都有很多“政绩”,其实有价值的东西不多,尤其从根本上进行创造的东西几近于无。
中国的大学现状如此,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人应该严肃地想想:我们民族、国家的未来还会剩下什么?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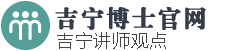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