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办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COP15),最终以乏善可陈、没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结束,这些协定使人们对《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s)强壮继任者的迫切愿望遭受重创,尽管如此,本次大会的召开,形成了很多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玩家”——自行做出重大承诺的强劲势头。
沃顿商学院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埃、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全球环境领导力计划”(Initiativ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简称IGEL)的主任里克•奥兹(Eric W. Orts)认为,尽管未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协定,不过,减少温室气体的行动已经在实施了,这些行动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将会日益增加。此外,虽然华盛顿尚缺乏决定性的政治突破,不过,范围广泛的国内规章和国际规章很可能会相继出现。再有,从长期来看,由某些国家、非政府组织(NGO)和大型公司参与其中的小型“气候协议”(climate contracts),很可能会成为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促进力量。
哥本哈根大会取得的进展和结果让观察家们普遍感到不满。尽管参会各方都坚称,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而且反复申明,应该把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控制在不高于工业化前全球平均气温2摄氏度(3.6华氏度)的范围内,但是,他们并没有为完成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所需的大量减排设定时间表和规则。可持续发展研究所(the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在哥本哈根大会提出的目标与各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承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个研究小组认为,如果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那么,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会上升7华氏度。
沃顿商学院名誉教授和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可持续发展教授保罗•克林多佛尔(Paul R. Kleindorfer)出席了这次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会议组织地很糟糕,此外,在奥巴马总统到会之前,大会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进展。”他谈到。“奥巴马总统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但也只是取得了十分有限的进展,而在消除‘南北分歧’方面,则没有什么进展。”尽管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修订的《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和能源法案》(Waxman-Markey climate and energy bill)(该法案由亨利·瓦克斯曼(Henry Waxman)和爱德华·马凯(Edward Markey)提出,故得名。——译者注),但美国参议院近期尚不会通过全面的气候法案。可以理解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已成为全球变暖的最大威胁——担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会制约它们的经济发展,并降低它们消除贫困的能力。
但是,美国行政部门取得的成就则是巨大的。奥巴马总统的计划已经重塑了商业环境(尤其是能源行业和汽车行业),各州或单枪匹马,或结成区域同盟,已经向气候变化发起了进攻。
同时,无数行动也已经在国外启动,尤其是欧洲,不过,第三世界也一样。在走向哥本哈根之前,很多国家都做出了承诺。根据《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的条款,到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将被限制在3.6华氏度以内,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高级研究员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认为,如果17个最大经济体信守自己已经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那么,达到全球平均气温控制目标所需的减排量就能完成65%了。
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
最近,中国超越了美国,成了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在人均排放量上,美国依然名列前茅,而中国远远居后。)。印度在经济活动和温室气体排放两个方面也在迅速增长。但是,因为它们认为,工业化国家应该为现在大气中存在的大部分二氧化碳负责,所以,这些排放大国的大量减排之路并非坦途。
“现在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企图,那就是将负担和责任转移到新兴市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主席R.K·帕乔里(R.K. Pachauri)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但是,这些国家依然拥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也是事实,尤其是印度:还有4亿人用不上电。所以,在我看来,给它们消除贫困、创造发展机会的道路强加任何东西,从道德上来说都是错误的。”
然而,在哥本哈根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印度政府承诺,到2020年,“碳浓度”(carbon intensity)(指单位经济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20%到25%。这个承诺虽然不会减少总排放量,但是,它会显著降低排放增长率。中国同样宣布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碳浓度降低40%到45%。
要想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限制在3.6华氏度以内,全世界需要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如果中国能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单单是中国的减排量就能占到其中的25%,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的首席经济学家法蒂·比罗尔(Fatih Birol)谈到。但是,国际能源署还认为,如此庞大的减排量还只是理论上的,而且需要中国在能源部门投资4,000亿美元。谈判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症结问题是核查,因为不需实际采取任何明确的减排措施,通过报告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就能达到碳浓度降低的目标。所以,建立一个第三方监督机构就成了哥本哈根的一个主战场。
目前,人们逐渐达成共识的一点是,气候变化对富国和穷国的影响是一样的,工业化国家应该打破阻碍谈判进展(以及导致人们从气候大会退席)的僵局,同意为发展中国家捐助执行费用。印度环境部长伽瑞姆·拉梅什(Jairam Ramesh)在宣布新目标的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谈到,他的国家不会同意从法律上约束减排——但是,如果有外部经济援助,那么,可能就会更进一步。
在居于先导地位的“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简称G8)中,一个渐趋一致的意见是,2012年之前,八个国家每年将提供100亿美元专款,用以抵消最易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遭受的气候影响,同时用以补偿他们因为减排行动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拉梅什之所以发表上述声明,一定是受到了八国集团这一共识的鼓舞。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则以某一特定的数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未来三年中,提供13亿美元的专款。
奥巴马总统也承诺,美国也会为专项基金提供数额不定的捐助,他宣称:“提供这种援助不但在人道主义方面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也是在我们的共同安全上投资,因为如果我们不帮助所有减排的国家,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大会召开期间,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为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技术援助的基金捐助了3.5亿美元。美国进步中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奥巴马权力移交团队联席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称,奥巴马政府的承诺是个“游戏规则的改变者”(a game changer)。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一个应对全球变暖非常有效而且也在不断强化的监管战略,就是阻止森林砍伐(因为树木担当着“碳吸存”(carbon sinks)(也称为“碳汇”)的角色。)。美国环境保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简称EDF)国际理事会的安妮·佩特桑科(Annie Petsonk)认为,全球反森林砍伐协议的前景非常乐观。就像为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支出提供补偿一样,该协议也会为同意不再砍伐其森林的当地社区给予补偿。
《科学》(Science)杂志最近发表的一项对286个亚马逊流域社区进行研究的成果表明,当地从砍伐森林中获得的短期经济利益很快就会逆转。这篇文章估计,取消巴西森林砍伐所需的费用相对很少:只比这个国家目前的预算出超70亿到180亿美元,而结果则相当于全球碳排放减少2%到5%。
“即使所有其他措施都陷于停滞,‘联合国减少发展中国家伐林和林地退化造成的碳排放计划’(the United Nations initiative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简称REDD)也能切实向前发展。”佩特桑科谈到。“这一计划与美国《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和能源法案》条款的联系非常紧密,同时,在很多地区,都有为禁伐森林减排提供融资的市场渠道和非市场渠道。”
美国可能采取的行政措施
美国最高法院(The U.S. Supreme Court)在2007年马萨诸塞州状告美国环境保护总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的案件中裁定,在《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的框架下,二氧化碳(全球变暖的主要气体)被认定为一种污染物,美国环境保护总署有责任对其排放实施监管。继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以后,12月7日,美国环境保护署最终正式宣布,温室气体(对环境、美国公众的健康和福祉)构成威胁(并需对其排放进行监管),从而,为奥巴马政府出台温室气体减排行政命令,并在《清洁空气法案》的框架下进一步制订行政规章扫清了道路。在这项裁定宣告不久以后,奥巴马总统(携与他站在一起的汽车制造商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便于5月宣布了联邦环境保护总署历史性的规章(到2016年,每加仑汽油的行驶里程要达到 35.5英里。),以监管燃油的经济性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安全气候运动”(Safe Climate Campaign)负责人丹·贝克尔(Dan Becker)认为,即使没有国会的立法,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也为奥巴马总统赋予了遏制全球变暖趋势的授权。“只要大笔一挥,他就可以付诸行动了。”贝克尔谈到。“现在,无需等待国会的批准,他就可以发布行政命令了。”
奥巴马总统是带着到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17%的承诺走向哥本哈根的,这一基于《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和能源法案》的具体目标已在众议院获准通过,并有望很快在参议院进入立法程序(今年夏季,将最终进入国会立法程序),最终减排比例可能会降低。
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Princeton’s Woodrow Wilson School)地球物理和国际事务教授迈克尔·奥彭海默(Michael Oppenheimer)指出,国际性协定需要很长的批准时间,他认为,行政命令是更快付诸行动的强大工具。“未经国会的立法程序,总统只能走那么远。” 奥彭海默谈到。“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凭借行政权力,无需等待国会的批准,奥巴马政府就可以完成而且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比如,出台燃油经济性标准/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很可能还会在行政层面出台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命令,尽管这些命令显然缺乏国际性的约束力,不过,它们都是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和全球性政策的前奏。这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议题,要想取得进展,必须立刻在多条战线行动起来。
其中的一个命令就是以减少燃煤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目标的。贝克尔认为,只要将100个最大的燃煤发电厂转变成天然气发电厂,就能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5%。
总量控制与交易:有效的改革措施,还是官僚主义的噩梦?
美国能源和气候议案——如果它们能得以通过的话——在尺度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碳税”(carbon tax)最容易执行,但却很难赢得政界的赞同。有人担心,一个从政治上更能得到认同(但同时也更复杂)的议案,同时也是《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和能源法案》列明的“总量控制与交易”(cap and trade)体系,容易被人操纵。
宾夕法尼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Penn’s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机械工程和应用力学教授、全球环境领导力计划的成员诺姆·利奥尔教授(Noam Lior)认为,碳税有很多反对者,因为它更简单易懂。“碳税是最简单易行的手段,但是,从社会和政治角度而言,征收碳税困难重重。”他谈到。
利奥尔对《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Clean Water Act)(20世纪70年代初,这两个法案均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期得以通过。)赞赏有加,他还就支持环境保护法规和法规执行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类比:“我们都应该知道,而且也都应该接受的是,哪怕你只是将一个口香糖包装纸扔到车窗外,你也会被罚款500美元。”从大烟囱排放的气体,造成了地方空气污染,并使全球变暖愈演愈烈,最便宜的能源生产方式——毫无疑问是燃煤——也是最脏的方式。利奥尔认为,法规应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必须建立某种鼓励高碳能源经济转变的机制。”他谈到。
宾夕法尼亚大学地质和环境科学系名誉教授、全球环境领导力计划成员罗伯特·基格盖克(Robert Giegengack)对此表示赞同。“真正能取得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向碳排放征收可观的累进税。” 基格盖克认为,另一种主选方案,也就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会“导致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出现。”
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策略,需要政府设定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总量的上限,之后,将排放许可分配给各个公司,允许每个公司在限额以内设定自己的排放量。如果某个公司的排放量超过了它持有的“排放信用”(emissions credits)允许排放污染物的上限(那么,它就将被课以罚款。),它可以从在开放的市场中,从其他在环境保护上表现更好的公司那里购买更多的排放信用。这样,当某些公司——出于各种理由,发现自己能轻松减少排放量的公司——将自己多余的排放信用,卖给那些很难减少排放量的公司,从而,使后者的排放量被冲抵时,总排放量就能达到我们希望水平了。所有这些环节都需要通过一个排放市场机制得到实现。
基格盖克认为,“经济学家、律师和政治家会抢占有利地位,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将限额设定得很高。每次碳排放信用的转移,都会有两名律师介入其中。所以说,总量控制与交易对律师来说,就像燃料乙醇对农场主的作用一样,它在二氧化碳排放上的作用并不比燃料乙醇更大。”
利奥尔虽然也有些同样的担忧,不过,他对这一机制的长期收益表现得更为乐观。“总量控制与交易确实有某些缺陷,它会让企业将更高的成本以更高的能源价格形式转嫁给消费者。”他谈到。“不过,因为这会减少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此外,因为竞争者会以更低的价格参与进来,所以,从长期来看,这并不是什么问题。”有些竞争者会来自可再生能源领域,它们在总量控制与交易的框架下能获得商业上的优势。利奥尔谈到,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措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很快就能在法规中发现漏洞,并利用这些漏洞为自己谋利——就像我们在安然公司(Enron)丑闻中看到的一样。那么,你怎么纠正人们的抱怨呢?你会制造多少官僚主义呢?”
尽管存在着这些疑虑,不过,政治的力量正在推动碳交易(为了避免使用“税收”这个词汇而采用了一种自由市场解决方案)的发展。“总量控制与交易是世界前进的方向。”奥兹谈到。“我们可以就总量控制与交易政策与碳税政策相比的优点展开争论,我对这个政策将来怎么运作也有些担忧,但它却是排队等待核准的主要机制。”
总量控制与交易在欧洲已经被制订成了法律,其结果喜忧参半。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研究,到2007年,在参加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所有公司中,有65%的企业是基于碳排放的价格来制订投资决策的——“这正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反应”。但是,《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称,“欧盟启动了一个远大的生态目标:通过让它们为每一吨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付费,而鼓励公司削减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该计划引发了一场游说混战,并导致了政治家为各个企业施惠的行为,从而破坏了环境保护目标。情况已经变得很明朗了,那就是,截止到目前,这个体系对遏制气候变化并没有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反倒给这个大陆的某些污染大户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意外之财。
虽然尚没有联邦法令,不过,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在美国已经开始运作了。10个州达成的协定——区域温室气体计划(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简称RGGI)——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东北地区和中大西洋区域发电厂的排放量。交易始于2009年年初,目标是,到2018年,发电厂减少1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德克萨斯州之后的第二大排放者加利福尼亚州,也推出了一个地区性的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该计划将于2012年实施。
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监管计划(Penn Program on Regulation)负责人卡里 ·科格里安内斯(Cary Coglianese)认为,这些地区性的计划会造成“反效果”。“地区性和各州的计划正在使联邦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变得复杂起来。”他谈到。“一个问题是,人们看到这些行动以后会认为,不需要再推出全国性的计划了,这是个错误。”现在有20到25个州设有气候变化法规,科格里安内斯谈到。
刊登于2008年一期《康涅狄格法学评论》(Connecticut Law Review)上一篇由科格里安内斯与乔斯林·德安布罗西奥(Jocelyn D’Ambrosio)合写的文章认为,“无论权力下放的经验主义在其他条件下有什么样的长处,但是,它就是不适用于全球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实践。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需要一个全面的、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是,逆转温室气体排放的趋势和影响则必须要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科格里安内斯还谈到,总量控制与交易最有效的实施方式,应该是专注于数量较少的“上游”源头(比如,发电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采矿业和炼油业。),而不是在排气管的层面针对无数“下游” 用户的排放。“我们所有的汽车、所有的办公楼以及所有的住房都是碳排放源,所以,专注于数千个温室气体排放源头要容易得多。
为碳排放定价的另一种方式源自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这位杰出的气候科学家是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所(NASA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的负责人。作为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的批评者,汉森提出了一个名为“费用和红利”(fee and dividend)的替代性方案——也就是逐渐提高碳税的方案,对矿物燃料(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在“入境口岸”征税并将税收集中起来。这些统一以每吨二氧化碳表示的“碳费”,将会以红利的形式返还给公众(并能抵消传递给他们的、不可避免的能源价格上涨)。“随着时间的延续,”汉森谈到,“矿物燃料的消耗就会大幅减少。”
汉森的专栏文章激起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强烈反响,他指责汉森“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去弄清排放控制经济学。” 克鲁格曼认为,无论是碳税,还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最终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唯一的区别在于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何在。”他写道。“如果你采用碳税政策,那么,你会知道排放的价格是什么,但你不知道排放量是多少;而如果你采用总量控制政策,那么,你会知道排放总量,却不知道排放的价格。”从根本上来说,克鲁格曼更偏爱总量控制与交易政策,因为“在灾难变得无可避免之前,这是我们在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机会实施的唯一行动。”
奥兹同样也强调了专注于温室气体重点排放源的好处。尽管他也支持制订一个国际条约,不过,他补充谈到,自上而下的方式,其效果最终可能不如众多的“气候协议”更好,他所谓的“气候协议”是指在非政府组织和大型公司之间(沃尔玛(Wamart)与美国环境保护基金(EDF)达成的“绿色供应链”(greening the supply chain)协议就是一个例证,以及在主要国家之间达成的独立减排协议。“如果中国和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合在一起占全球总量的40%,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5%,”奥兹谈到,“我们就需要涵盖范围广泛的多种气候协议,以将我们引向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所谓的‘引爆点’(tipping point)(这个语汇源自他的著作《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
见识了哥本哈根的僵局之后,克林多佛尔认为,主协定的附属协定无需将出席本次大会的192个国家全都牵扯进来,这样协定能产生更显著的成效。“30个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90%,它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谈到。“这30个对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负主要责任的国家,可以在2010年进入紧迫的议事日程——制订共同的规则,并在碳排放定价上达成一致。”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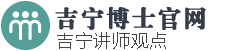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