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加拿大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是管理学界的叛逆者。他是“管理者角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核心贡献是对管理者工作的分析。本次刊发的《雕琢战略》是其管理思想发展路径上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
在文中,明茨伯格颠覆了传统战略观点,指出战略应该是一门手艺,是心行合一的产物。基于此文接受本刊采访的明茨伯格先生还明确指出:中国不应该照搬欧美的管理模式。为了中国管理者对明茨伯格有更加清晰的认知,本刊还特邀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肖知兴先生撰文,介绍明茨伯格在管理学的思想脉络和管理教育上的探索。
想象一下,战略应该是怎样被“计划”出来的?很有可能,浮现你眼前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位高管,或者几位高管,坐在办公室里程式化地规划着一系列公司的行动方案,所有人都必须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些方案。“计划”的重点在于理性:理性地掌控全局,系统地分析竞争对手、宏观市场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局限,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这群人就能“想”出来一个明晰、完整的战略计划。
再想象一下,如果将战略视为艺术家雕琢作品,那它应该被如何“雕琢”出来?与机械的计划相比,这将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手艺活可是要结合传承的技艺、倾情的投入以及专注于细节的完美追求。“投入”与“理性思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经过长时间的经验和感性认知的积累,你应该能够感受到手指接触到材质时细腻的触感,以及人与物的和谐统一。而战略的成型和实施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创造性的战略也由此生成。
我的观点很简单:“雕琢”一词更灵动地抓住了有效战略制定这一过程的精髓,“计划”战略则曲解了战略制定的过程,而且不可逆转地误导了公司运用它的方法。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观点,我想拿陶艺师打个比方。我把一些公司几十年以来的战略制定与陶艺师的经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两者工作的背景完全不同,就和我的观点一样,貌似不着边际。但如果我们把一个公司看作一位陶艺师,我们会发现他们所面临和试图解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是否足够了解自身(或组织)的能力并能依此找到战略的方向。从“人”的角度来考虑战略的制定,抛弃所谓“装备齐全”的战略咨询产业,我们才能真正认知公司是如何形成战略的。
静坐在转轮和陶泥前,陶艺师头脑中构思着这摊陶泥将要呈现的样子。她非常确定,自己当下的操作在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许之间的平衡点,她对过去的成果和遗憾都了然于胸,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市场有着明确的把握——这些就是陶艺师的感知,而非其分析。所有的了解、知晓、把握,都无需用言语表达。这些想法在她脑中浮现的时候,也已经在她的手上成形。转轮上的成品或许和她过去的作品雷同,但她也可能另辟蹊径、不落窠臼。即使这样,你也会在当下的作品中发现她过去的影子和对未来的追求。
我把经理人视为陶艺师,而战略就是他们手中的陶泥。和陶艺师一样,他们就在公司现有能力和未来机会之间。如果他们真的是能工巧匠,他们对信息的了解就会和陶艺师对手上的陶泥的把握一样——这才是雕琢战略的关键所在。
对于“战略是什么”这一问题,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计划”、“行动指南”之类指导未来的东西。但当你再问,一个公司、政府或者你自己真正执行的战略是什么,十有八九他们会有另外一种答案:过去一以贯之的行为模式。最后你会发现,战略,说起来是一回事,做起来另外一回事——莫辨差别,毫不自知。
原因很简单,“战略”的规范定义早已偏离了希腊语词源的本意——解释过去的做法以发现未来的行为。无论如何,如果战略可以被计划、被设计,那么它就可以被贯彻和实现。行为模式,或者说实现了的战略,可以解释你未来的意欲所为。而计划,不需要产生一种模式,同理,模式也并不依赖于计划。一个公司可能有自己一贯的行为模式(已经实现的战略)。但对此,他们并不自知,更不用说用言语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其实,找到公司的行为模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根据我们的研究,像大众汽车公司和加拿大航空公司这样的巨头,找到模式和规律更容易。
读懂公司的“心”
传道解惑,让我们绕开人为复杂化的战略制定过程,回归到最基本的概念上——思考和行动的同一性——这是手工艺的根本,也是雕琢战略的关键。
实事求是地说,所有关于战略制定的文字都把此过程描述得复杂繁琐,甚至是故弄玄虚。
陶艺师在她的工作室,计划做一个圆形的作品,当陶土随着转轮旋转起来,一个圆形的物体出现时,艺术家或许想“那为什么不做一个圆柱形的花瓶?”一个想法跟着另外一个想法闪现,直到一个新的形状形成。行动驱动着思考——战略由此而生。
理想的商业世界中,当销售人员拜访客户,发现产品不符合要求时,他们会一起寻找修改方案。然后销售人员回到公司推进这一修改计划,经过二、三轮的讨论,最终交付符合要求的产品。一个全新产品可能由此诞生,并最终打开了一片新市场。事实上,在此过程中,这个公司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战略路径。
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销售人员并不这么幸运。如果一个公司战略的执行和制定是同一个人,那么融入创新的想法可能会变得简单而迅速。但在大公司里,有创新想法的人可能比发号施令并能将想法兜售给同仁的领导低十个等级。
当然,有些销售人员可以独立行事,亲自修改产品来满足客户需求,并说服工厂生产出来。从效果来看,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战略,哪怕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但有时候,公司的主流战略却因此瓦解。只有当领导者不得不寻求新想法时,他们的创新才可能被发现。那时,销售人员的战略才被贯彻于公司体系之中。
想想加拿大国家电影局采用的故事片策略。作为政府机构,加拿大电影局以创意闻名,擅长制作短纪录片。多年前,他们资助了一个项目,一位导演出人意料地制作了一部电影长片。为了这部电影的发行,国家电影局不得不转向依赖电影院,当然也无意中获得了制作长片的市场经验。其他的导演也循着此路,最后国家电影局发现他们已经开始了制作电影长片的战略。
我的观点很简单,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简单:战略可以形成,也可以规划。一个已经实现的战略可以是在应对变化的环境中产生;也可以是经过深思熟虑,先长篇大论的阐述然后再去实施。但后者并不见得能获取预想的效果,其结果多是被束之高阁。
知行合一
没有陶艺师会今天构思而在第二天动手,陶艺师的思考与其操作紧密相连。与此不同,公司对于战略制定的思考和执行经常是分割的,这就割断了两者之间交流反馈的关系。发现客户需求的销售人员,能提供对整个公司都有战略意义的信息,但如果他不能形成应对变化的战略,或者因为言路堵塞不能将信息传递给相关人士,这些信息就是无效信息。将战略视作阳春白雪的理念,脱离了日常的组织工作——这是传统战略管理最大的问题,同时也是大多数商业和公共政策战略失败的主因。
在麦吉尔大学,我们把国家电影局没有明确意图的战略称之为“应急战略”。这些应急战略也可能在被清楚认识到并被高层认可之后,变成深谋远虑的战略,但这是后话。
战略性学习
下面是陶艺师经常遇到的情况:陶艺师想要做一件独特的作品,但并未成功,所以她在尝试着弄圆或者弄扁。结果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还不完美,于是她一次次的尝试,直到几天后、几个月后甚至几年后,最终她会做出来她想要的作品——这时她已经换了一个全新的策略。
其实陶艺师创作的历程揭示出战略制定的两种路径。在实践中,战略的制定是要两条腿走路的:“深思熟虑”加上“应急战略”。一个单纯靠深思熟虑得出的战略会排斥吸收信息的学习过程,同时单纯的应急战略则极有可能失控。学习和控制必须并行,这就是为什么麦吉尔大学把“深思熟虑”和“应急”两种行为都称之为“战略”的原因。
1952年,电视节目开始在加拿大出现,国家电影局的高层并不热衷于制作电视节目。但当大家还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一位导演悄悄地为电视节目制作了一系列作品,有了先例,同仁们纷纷效仿。短短的几个月之后,管理层就决定他们要规划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全新战略,并将其作为长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共识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事实上,这是多位导演独立决定促成的结果。
虽然国家电影总局的战略规划看起来像是一个特例,但它确是很多组织中悄然存在的行为方式。你在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Pascale)记述的本田摩托车在美国市场上的成功案例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模式。虽然事后复盘,你觉得这个战略精妙绝伦,但最初本田管理者的战略计划几乎犯了所有可以预想的错误,直到他们的战略被市场彻底击垮。在美国的本田公司销售经理只得亲自驾驶他们的摩托车,然后做了惟一一件对的事情:从实际情况中学习,获得一手资料。
草根战略法
这些战略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我们称之为“草根法”的战略管理。战略就像花园里的野草,它们可以在任何土壤里扎根生长。人们有能力在处理具体情况时学习,并从环境中获得资源支持。当形成合力时,这些分散的认知就变成组织行为,并扩展成为指导公司的整体战略。
试想一下“伞型战略”的操作方式:高层设定了一个宽泛的指导原则(比如,只生产利润丰厚的高科技产品),然后把具体的细节留给下一级别的部门去处理(比如,这个产品究竟是什么)。这个战略的深思熟虑部分体现在高层的指导原则上,应急部分体则现在具体执行上,而且因为这个过程允许在运作中形成战略,所以我们称它是“深思熟虑应急法”。
深思熟虑应急法,也被我们称之为“过程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能够控制战略形成的过程:关注结构设计、人员配置、进展步骤等,同时把具体的内容留给其他人处理。过程战略和伞型战略在商业世界都很流行,但这要求兼具专业能力和创造性。像3M、惠普、国家电影局这样的公司和组织,能够有效运用这种战略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战略执行者和发布者是同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在公司的等级结构中的底层,他亲自处理具体的情况,还具备必需的技能专长。一个公司如果可以像陶艺师一样,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该是战略制定者。
传统的战略管理观点认为,变化是惟一不变的事情,公司必须随时适应变化——战略计划理论的文章尤其愿意强调这点的重要性。但这个观点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战略这个概念本身追求的是稳定性,而非变化。这类文章也强调,公司要寻找战略方向、部署实施阶段,并从公司员工共通的、已有的行为中寻找战略合作机会。无论哪种论调,根据定义,战略都是用来维持组织稳定性的。没有稳定性就意味着没有战略——没有通向未来的步骤,也没有从过去习得的模式。的确,说清楚一个战略本身就是为了防止战略发生转变。
以前的观点没能抓住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何时,或者如何驱动变革?战略制定的根本困境在于需要平衡稳定和变革两种力量——一方面关注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平衡再次投入与现金流的比例以适应外部的环境变化。
量子跃迁
我们还是很容易区分公司的稳定期和变革期的。
魁北克的斯坦伯格公司是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从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60年间,该公司经历了两次转型。1933年,这家连锁超市变为自选超市,1953年又转型为购物中心并成为上市公司。德国大众汽车也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70年代间,完成了一次战略方向转变——从传统的甲壳虫变为奥迪。加拿大航空公司40年来从未进行战略转变。
丹尼·米勒(Danny Miller)和彼得·弗里森(Peter Friesen)是我在麦吉尔大学的同事。他们在研究了大量的公司历史之后(尤其是业绩表现很好的公司),发现公司转型是有规律可循的,并以此创立了战略变革的量子理论。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公司在稳定期和变革期会运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绝大多数时期,公司遵循一个既定的战略方向。尽管总会有变动,但是这些变动都是在战略方向所许可的范围内(比如,完善一个既有的零售方案),通常只是在同一方向上持续增加、累计或者改善。大多数公司喜欢这种稳定阶段,因为这是在不改变战略、利用既有战略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就和陶艺师一样,他们通过运用自己独特的能力在既有的路径上逐渐改良。
但是,时光流转,世界不停在变,区别仅仅是渐变还是突变,因此公司的战略方向迟早无法与环境的变化同步。这时米勒和弗里森提出的战略革命就会发生。长期的、进化式的改变就会突然被剧烈的革命性骚动打断,公司会迅速改变很多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实际上,公司正努力奔向另一个稳定期,为此,公司必须迅速从战略、结构和文化中建立和整合一系列新的规范。
那些在组织里野草一样生长的应急战略呢?量子理论证明,真正的创新就藏在公司的某个角落,直到战略革命成为必然的选择。那时,绞尽脑汁或者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来的创意,都会成为新战略的备选,公司同时会寻找内部已经出现的模式,并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当旧有的、已然存在的战略瓦解之时,正是新战略的种子飞速生长之日。
战略革命的量子理论尤其适用于业界地位稳固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因为大多更依赖于标准化的程序,所以他们本能地排斥急剧的战略转向。所以我们发现长时段的稳定期会被革命性的变化突然打破。
大众汽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期以来备受宠爱的甲壳虫汽车以及与之配套的稳固战略,让公司忽视了市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市场变化。尽管公司领导层的愿景最开始使得战略能够有组织地推行,但当它与大型制造业企业内的官僚力量结合后,就变成渐进式变革的阻力,因此当变革终于到来时,其战略就成为大众汽车的灾难:在确定新车型之前,公司产品经历了一段“大杂烩”的时期。说到底,战略转向是一场文化革命。
找到自己的模式
无论是在曼哈顿的高管还是蒙特利尔的陶艺师,战略管理的关键是找到已有的模式,并将其发展成型。经理的工作不是预想出某个战略,而是识别出已经在组织内出现的战略并适当地干预。
就像花园里不经意出现的杂草,有些应急战略需要马上被连根拔除,但是管理层不要太急于铲除意料之外的应急反应,今天的歧路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方向(在欧洲最受欢迎的沙拉,食材是蒲公英叶子,而蒲公英在美国被认为是最令人讨厌的杂草)。有些模式值得在实际奏效之前长期关注。真正有效的模式需要认真思考、仔细研究并正式融入战略计划中,这需要动用伞型战略来执行。
这样的管理模式要求创造出能够滋养各种战略的土壤环境。在复杂的组织中,这意味着创建弹性结构、雇用创造性人才、定义伞型战略,从而发现正在萌生的模式。
正如坐在转轮前的陶艺师一样,公司必须要了解过去才能管理未来。只有理解了他们自己的行为模式才能知道他们的能力和潜力。雕琢战略,就像管理艺术品,这是对未来、现在和过去融会贯通、自然而然的理解。
(原文刊载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1987年7、8月合刊,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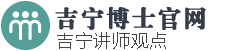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