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着公司厚望的“梦幻客机”波音787自诞生之日起,就被预算严重超支和电池起火事故等问题困扰。产品出现技术问题并不罕见,但其特殊之处在于,问题源自华尔街。正是在华尔街的重压下,波音高管才做出了有害公司的决策。
在1997年并购麦道公司之前,波音公司一直以工程技术为先的企业文化和大胆投资新机型的历史为荣。与之相反,麦道公司以风险控制、削减成本和关注财务表现著称。并购完成后,麦道保守的企业文化渐渐在新合并的公司占据主导地位。不顾资深工程师团队的反对,波音公司破天荒地采用全球供应链模式,将787的大部分零部件生产外包。一些工程师认为其目的是要最大化公司的净资产回报率(RONA),提振公司股价。外包确实削减了公司的资产规模,但也使787的供应链变得无比复杂,导致公司难以保障客机所必需的极高产品质量要求。果然不出工程师所料,787的开发周期一拖再拖,预算严重超支。
波音保持最低限度资产的决策与华尔街密切相关。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经常用净资产回报率来判断公司及其表现。华尔街对这些财务指标的偏执严重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运作。经济学家约翰·阿斯克尔(John Asker),琼·门萨(Joan Farre Mensa)和亚历山大·永奎斯特(Alexander Ljungqvist)的研究显示,为了追求短期内股价的最大化,上市公司对资产的投资额只有非上市公司的一半。面对减轻资产的压力,美国莎莉集团从食品服装制造商转型为纯粹的品牌管理公司。莎莉集团的CEO对此解释道:“华尔街掌握生杀大权。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只会奖赏那些用最少的资产获得最多利润的公司。”尽管研发和制造的紧密结合是创新成功的关键,但为了追求更高的股票收益,很多像波音和莎莉集团这样的公司不得不将制造环节外包。
在前一篇文章中,克里斯坦森认为管理者对华尔街标准的追捧会遏制创新。实际上,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对华尔街多有怨言。他们认为华尔街不但鼓励短期投资行为,更会为了股东而牺牲员工和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它还助长高管的不诚信行为,因为后者常背负不可能完成的业绩目标。最近一项针对CFO的调查显示,为了达到华尔街的财务目标,保持稳定的财务表现,78%的CFO会“在长期价值上让步”,55%的CFO会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面对华尔街的压力,这些CFO会故意置公司利益于不顾,金融业对管理者影响力之强可见一斑。
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高管的唯一职责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自此委托-代理理论成为职业经理人的信条。对华尔街俯首帖耳的高管常常辩解自己对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有不可推卸的“信托责任”。然而问题是,这种责任并不存在。信托责任特指一种法律上的义务,与高管职业道德责任无关。企业法学教授琳恩·斯托特(Lynn Stout)的著作就指出,美国高管从未面临此类的法律要求。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如此明显的谬论?为什么管理者会作出那些明知错误的决策?就像经济学家谈论金钱,士兵谈论武器,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权力是我的我研究对象。因此我将从权力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解析。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或者国家会做出有损自身利益的行为。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状况是某个领域或某一群体获得压倒性的权力,因为他们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自我认知。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必须要制衡华尔街过于膨胀的的权力金融业再“崛起”。
在大萧条前的时代,金融界人士拥有极强的影响力。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曾发起一项针对J.P.摩根铁路业务的反垄断诉讼。不可一世的摩根竟然没有亲自露面,他告诉罗斯福:“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对,把你的司法部长派到我这里来,我的人会修正的。”1929年股灾后,为了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 Act)等诸多法案。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这些法案大多已被废除或名存实亡。这直接引发了金融业的快速扩张。1950年,金融和保险业只占美国GDP的2.8%,到1970年,升至4.2% ,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6.6%;1970年,美国金融保险业的利润相当于其他所有行业利润总和的24%,尽管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数字在2013年已上升至37%。
实际上,这些数字并没有完全展现金融业的压倒性地位,因为它们并未涵盖众多非金融机构的金融部门。自20世纪80年代起,非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部门开始快速发展,到2000年,这些部门的金融资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所述企业的实体资产。当时福特在债券市场的收益已经超过其汽车业务。GE资本为GE电器贡献约一半的营收。如果将这些金融业务部门计算在内,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就相当于当年GDP的5倍。2007年,这一比率已上升至10倍。
规模和利润的不断扩大也强化了金融业对政府的影响力。1998年至2013年,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业在政府游说上总共花费了60亿美元,仅次于医疗健康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业加强了对政府的金元攻势。截至2014年3月的2013-2014选举期,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业就已经花费了4.85亿美元用于政府游说,超过其他所有行业。此外它们为联邦职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献了1.49亿美元,相当于医疗行业捐献额的3倍。
金融业的代表和说客常常与金融监管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华盛顿政界将之称为“共生体”。这点从现任和卸任政府官员的履历中可见一斑。让我们列举美国近6任最高金融监管者——财政部长。现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曾经在花旗集团供职;其前任蒂莫西·盖特纳现担任美国私募机构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总裁;再之前的汉克·鲍尔森曾是高盛CEO。再之前的约翰·斯诺是私募机构 Cerberus的主席;拉里·萨默斯在卸任后从对冲基金D.E. Shaw处获得500万美元的酬劳;罗伯特·鲁宾出任财长前在高盛供职26年,官至董事会联合主席,卸任后他又出任花旗集团高管。
我的研究显示,这些领导者通向权力的道路对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人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沉浸在金融领域,有着同样的世界观。这6位财长有的在加入政府前就在金融圈声名显赫,有的则在任内对金融圈的利益表现出足够的重视,离任后轻松获得金融机构的高薪职位,有的两者兼备。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Bair )解释道:“这是一种认知控制,与腐败的关系不大。他们只是不停地受到大型金融机构的影响,对金融领域以外的关注远远不够。”
即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对美国政策依旧有强大影响力,以下是3个典型案例。
被认为是挑战华尔街利益的沃尔克规则的目的是要禁止持有联邦担保存款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华尔街想方设法地拖延该法规的执行。早在监管机构发布草案几个月前,金融机构的代表就开始行动,监管机构进行的外部会议中有93%是由这些说客安排的,这大大延缓了法规出台时间。
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危机的一大主因,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试图对衍生品进行监管。华尔街立即进行了一场地毯式游说,并因此获得了一系列的豁免条款,致使监管只覆盖不到20%的全球市场。
华尔街银行的规模让它们获得了巨大的特权——大而不倒。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曾经向国会提供证词:由于一些银行规模太大,对它们进行指控会伤害美国经济,他不得不放弃一些针对这些银行的诉讼。这意味着,这些银行变得无比强大,政府的最高执法者已将它们置于法律之上。
金融界的声誉和地位也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顶峰。在罗斯福新政后,华尔街被视为一潭死水。德鲁克在1949年写道:“20年前哈佛商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会争相为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工作,现在他们希望为钢铁、石油或汽车公司工作。”2012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摩根大通和高盛跻身全球10大理想雇主之列。同年35%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进入金融服务业。尽管这一数字稍逊于2008年最高峰时的45%,但华尔街依旧是哈佛商业院毕业生最佳的职业选择。
经济金融化及后果
经济金融化是指金融市场、机构和从业精英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其地位高于实体经济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社会机构。美国并不是经济金融化的孤例。以社会学家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为首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历史不同阶段的经济金融化例证,其中包括14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末的荷兰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在金融化过程中,英国和荷兰都察觉到这一现象并展开了关于经济转型的激烈讨论。那些腰缠万贯的金融精英凭借自己日益增长的强大财力怂恿本国政府将国家的前途押注于金融。1925年英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采取强势货币政策,让英国的金融服务业从中获益,反之弱势的英镑则会提振本国制造业。最终英国屈服于金融精英,选择了强势英镑政策。
金融本应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然而在金融化的经济体中,两者乾坤颠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强大的金融系统对国家经济起步和中期发展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当私营机构信贷达到GDP的80%至100%时,它就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2012年美国的私营机构信贷曾达到GDP的183.8%。除了对波音等实业公司的间接影响,高度金融化对经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危害。第一,金融系统规模越大、复杂程度越高,它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伊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拉古拉迈亚·拉詹(Raghuram Rajan)等众多经济学家都得出了这一结论。
第二,过度发达的金融系统会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早在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就曾观察到:“证券业所做的工作大多数与资助实体经济投资无关。”托宾对此困扰不已,他说道:“我们将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年轻人中的精英投入到金融活动中,它们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关联甚少,却获得了与自身社会贡献不成比例的巨大财富。”
这种状况部分原因源于资本。经济学家厄兹居尔·奥尔罕勒(Özgür Orhangazi)的研究显示,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金融资产的投资会慢慢抽走实体资产的投资,因为市场倾向于短期和流动性资产,非金融机构面临投资者回报(主要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的压力越来越大,无力收购实体资产。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当不仅限于资本,就像托宾所言,人才分配也面临这一问题。英国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Roger Bootle)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可分为“创造性”和”分配性”两类。创造性活动增加社会整体财富,分配性活动则只是将财富从一只手转向另一只手。每个行业都包含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金融业以分配性活动为主。
金融业有一种高端的分配性活动——“寻租”,即指通过操纵政策获利。经济学家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安德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惟施尼(Robert Vishny)指出,当一个国家最有效率的工作者从企业界转向“寻租”活动,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放缓。
华尔街就像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它吸走了美国最好、最聪明的人才,他们中大多数最终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当我们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为高频交易缩短1纳秒绞尽脑汁之时,谷歌就失去了一位工程师,我们也许就与下一个特斯拉擦肩而过。
我们还可以用交易的角度阐释这个问题。在一些行业中,大部分交易会为交易双方都带来价值,属于正和博弈。例如你从福特公司购买一辆汽车,对你来说,汽车比现金价值大;对福特来说,现金比汽车价值大。理想状态下,一年之后你和福特公司都会从中受益。另一种情况则相反,如果我向你出售股票,那么一年后我们中只会有一个人获益,这是一种零和交易。
金融领域中大部分活动,例如零售和商业银行、保险业和风投资本都属于前者。然而还有很多金融活动,例如投资银行主要从事零和交易,这些金融机构在放松管制后得到迅速发展。
薪酬是金融领域强大影响力的另一个缩影。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 )和阿里耶勒·雷谢夫(Ariell Reshef)发现,在大萧条之前,即便将教育水平因素考虑在内,金融领域从业者的薪酬也远高于其他行业。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生效,这种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到1980年差距完全消失。然而在放松管制后,情况再次逆转,到2006年这种薪酬差距又回到了大萧条前的水平。
2006年,金融业从业者的薪酬平均比其他行业同等教育水平的员工高50%。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这种差距更加悬殊——他们比其他行业的高管多挣250%,如果是在华尔街供职的高管,薪酬差距高达300%。在美国1980年以来收入不平衡现象中,这种悬殊的薪酬差距的“贡献率”为15%-20%(根据计算方式的不同)。
失衡害人害己
金融领域在经济中起到关键作用,现代经济体的存在离不开银行等金融机构。然而当它的规模过于庞大,它就会拖累经济的发展,加剧经济的不平等,并且一旦崩溃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灾难。2008年金融危机让美国政府付出了2万亿美元的税收,被迫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尽管弊端重重,金融领域依旧对实体经济体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会伤害企业自身利益,管理者依旧臣服于华尔街。我们不禁回到开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和整个社会会作出有损自身利益的行为?
答案就是权力的失衡。
黑洞可以通过引力让行星偏离轨道几光年,同样巨大的权力和声望也会直接和间接地改变周围人的行为。直接方式是通过强迫和利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政治捐助帮助政客赢得选票时,这种直接方式就会显现。
间接方式较为微妙,但影响力更强。真正的权力从来不是强迫别人,而是改变人们的思想,让他们自愿服务。阿克顿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通常认为这句名言是关于权力对其拥有者的影响。但实际上阿克顿真正要指出的是,权力会扭曲人们对掌权者的判断。人们天生倾向于相信,权力拥有者代表善良和正义,他们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实际上权力和声望会大大美化人们对掌权者的认知。
重权在握的社会群体还会影响人们的观念。这与腐败无关,人们的观点会自然地随着利益发生变化。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曾经说道:“当一个人的收入是基于对某一事物的熟视无睹,那你很难让他去理解该事物。”这导致整个社会为最强大群体的利益服务,进一步强化该群体的权力,形成恶性循环。
权力失衡会让整个社会面临灾难性后果,这种悲剧在历史中不断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军队和军工产业控制。当时德国对英国的殖民版图觊觎已久,无奈却忌惮于英国皇家海军的强大实力。尽管两国处于友好状态,德国军队决心建立一支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舰队。为此德国海军开始向政府施压提高海军预算,并建立新闻署来控制媒体报道。此外,海军还招揽德国最知名的学者为其喉舌,其中包括当时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结果海军预算大幅提高,进一步加强了海军对整个德国社会的控制。
英国将德国海军视为无法忽视的威胁,并因此与法国和俄国结盟。一战爆发后,造价不菲的德国军舰被封锁于近海,毫无用武之地。德国海军只好依靠潜艇,寄希望于削弱英国皇家舰队的实力。然而放任攻击商船的无限制潜艇战威胁到美国在大西洋上的航线,导致美国参战,加速了德国的战败。社会权力失衡导致德国在舰队上花费了大量资源,这些舰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还起到了反效果——将英国和美国推向德国的对立面。
相似地,美国的金融领域,尤其是华尔街掌握了失衡的权力。强大的金融领域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它就像经济的循环系统,将资本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大型银行驱动了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它们就像系统的心脏。美国经济已罹患“心脏肥大症”,它的“心脏”变得过大过重,不但拖累整个机体的发展,还影响了它的基本功能。
再塑平衡方案
我们需要重建社会系统的平衡。过大的规模和不合理的利润是金融领域权力和声望的来源,因此我们要在不影响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让其规模和利润回归合理状态。其中关键是要进行有益于经济价值的改革,限制那些由权力产生的扭曲行为。因为会限制金融业的权力和利益,这些改革必将会遭遇阻力,但这正是必须要改革的内容。。
经济政策对权力产生影响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历史一样长,它可以追溯到华盛顿的第一届政府内阁,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就因此相互对立。两人对美国经济的走向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既包含对民主的不同认识,也包括对财富产生方式的分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主要灵感来源于20世纪反垄断思想家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他认为大型金融机构会取得其他产业,甚至政府之上的权力和影响。
以下是改革的几个方向。
限制银行规模和杠杆率
放松管制后,美国大型银行得到快速发展,甚至超越了危机前的规模。1995年,美国最大6家银行的总资产相当于GDP的17%,2006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55%,2013年上升至58%。这些银行从政府获得了大量的间接补贴,市场因此得出结论,这些银行的债务已经得到了政府的保证,这降低了它们的借贷成本。2012年,美国政府对8大银行的补贴高达7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税收的2.5%。如果银行的规模得到限制,美国政府就会允许它们破产,从而限制它们的权力,减少政府补贴。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郭庾信(James Kwak)在《13个银行家》一书中指出,银行的总资产(包括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不应超过GDP的4%,投资银行的资产不应超过GDP的2%。这一政策只会影响几家银行,但这些银行却拥有强大的权力。
银行另一个加强权力的方法是提高杠杆率,这增加了利润但也让风险增大,杠杆率越高,银行的容错性就越差。当政府对银行进行紧急救助时,这种风险就被转嫁给大众。系统问题已显而易见,几个金融机构决策者造成的风险需要由整个社会买单。然而在政治权力的保护下,监管者对这些机构束手无策。在《银行家的新衣》中,经济学家阿纳特·阿德马蒂(Anat Admati)和马丁·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认为,如果将银行的杠杆率限制在3:1以下——股本占银行总债务的1/4以上,那么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同时银行的放债能力不会受到影响。
平衡债券与股票
目前债市的规模要远大于股市,债券产生的风险也远远高于股票。公司的借贷率越高,金融市场对它的控制就越强。很多CEO正是由于避免借贷过多,才打造了伟大的公司。然而美国税法规定,利息支付可以免税,分红则无法免税。这间接补贴了债市,损害了股市。税收优惠加上高昂的企业税导致很多公司倾向于借债。如果政府取消对债市的补贴,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控制就会削弱。我的同事罗伯特·波曾(Robert Pozen)建议政府应该在降低补贴的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对金融交易征税
金融领域另一利润来源是今天资本市场中巨大的交易量。尽管单笔金融交易的价值不菲,但这些交易会让全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减缓经济增速和周期性政府救助等。
此外,低廉的股票交易成本会鼓励投资者追求短期套利,而非长期投资。减少这些负面影响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征税。金融交易税能降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让投资者聚焦于长期价值,削弱金融业的权力。早在1936年,凯恩斯就提出了金融交易税的构想,1972年托宾曾实施外汇交易税。目前有40个国家征收金融交易税,美国也曾在1914到1966年间征收交易税。
提高资本利得税
目前资本利得的税率较低,这间接为很多金融机构提供了补贴。理论上,较低的资本利得税可以鼓励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然而现实中这种因果关系却非常薄弱。经济学家莱昂纳德·布尔曼(Leonard Burman)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研究显示,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资本利得税率没有关联。税率差意味着,收入源于资本的人获得的回报要远高于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人。这导致金融领域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管,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股票期权,高管也错误地认为让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其唯一责任)的税后收入大大增加,权力和声望随之大幅提升。为什么政府会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为金融从业者提供补贴呢?权力的失衡影响了政府的思维和政策,让它相信了一个看似合理,却充满漏洞的理论——较低的资本利得税能刺激经济发展,而实际从中受益的只有一小撮金融精英。
几十年来,美国金融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让最有权势的金融精英获得了巨大财富,并让美国企业和政府对其俯首帖耳。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化掩盖甚至损害了多数金融机构诸多的关键性活动,无论这些机构是零售及商业银行、风险投资还是保险评估机构。
非金融企业需要将恢复权力平衡作为重中之重。权力只能通过更强的权力制衡,尽管华尔街的势力非常强大,但构成实体经济的企业界拥有更大的力量。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大多数行业都存在过度监管的现象,只有金融市场的监管不足。对航空公司解除监管创造了市场奇迹,对银行解除监管却会带来灾难。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不同,因此也需要我们区别对待。美国企业界应达成共识,金融化会损害实体经济的运行,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
一些非金融企业已经开始反击。2013年《纽约时报》报道,大型金融机构利用手中铝储存仓库的所有权(高盛一家就拥有北美地区70%的铝储存设施)推高铝金属价格,从中获利。自2010年起,美国消费者因此总计损失了50亿美元。制铝企业因此提出上诉,导致参议院和美联储开始审核2003年颁布的允许银行进行实物期货交易的法令。企业界已经意识到,这只是华尔街势力的冰山一角,这些企业已开始推动政府对金融领域进行改革,并将其视为影响自身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
在这一进程中,领导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尽管领导者会受到环境的限制,但在正确时间、正确位置上的优秀领导者能改变一家公司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林肯在内战的战火中重塑了美国。老罗斯福在美国深陷大萧条之时带来了新政。领导者,特别是总统能够引领政治舆论,将国家带向新的政治均衡。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系统还过于脆弱,无法承受改革的冲击。2013年,金融系统欣欣向荣,华尔街从业人员的平均奖金高达16.5万美元,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收入中值停滞不前,这些信号都显示,美国经济在恢复之路上踯躅不前。不良的经济现象甚至出现常态化的趋势。
现状绝非无法避免。老罗斯福总统当时是这样回复不可一世的摩根先生的:“那可办不到,我们根本不想修正,我们要彻底终止这种行为。”两年后,老罗斯福政府彻底打破了摩根的垄断。今天的金融精英与摩根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摩根当时控制了美国40%的资本,但这也没有动摇老罗斯福的决心。
一切照旧的做法已经失灵。在危机前,旧有的做法就已失效,房地产泡沫掩盖了经济的深层问题。今天我们都已清楚看到,美国经济无法为人们带来充足的工作机会和合理的收入。我们能够重建社会平衡,从金融巨头手中解放美国企业,让它们恢复一直以来最擅长的工作——创造财富并造福于每一个美国人。我们能做得更好,选择权就在我们手中。(安健/译 牛文静/校 钮键军/编辑)
高塔姆·穆昆达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著有《不可或缺:领袖的闪光时刻》(Indispensable: When Leaders Really Matter,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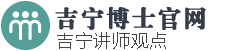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