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曾发明了火药、指南针、水车;纸币、票号、公务员与科举制度这些极具创造性的金融与教育体系也诞生于中国。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相比欧洲经济体更为开放,更加市场化导向。然而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西方才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发源地,中国只能培养出死记硬背、墨守成规的书呆子。在那里,人们虽然努力研发,却极少产生突破性的创新。
我们试图找到原因,但答案却莫衷一是。有些人将之归咎于工程师创业者。动点科技(TechNode)网站编辑杰森·林(Jason Lim)认为,“大多数中国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不是设计师或艺术家,而是工程师。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缺乏创造力,想不出新点子或新设计。”
另一些人则指责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致使侵权事件规模空前。他们指出,盗版苹果产品并非中国独有,但只有在中国,冒牌的苹果专卖店堂而皇之的经营,而且店内员工都以为自己真的在为这家美国公司工作。
还有一部分人抱怨中国的教育体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Ichisada Miyazaki)将当代中国的应试教育称为“中国的考试地狱”。当学生把全部精力用于提高考试成绩时,他们怎么可能成长为创新者?
本文三位作者在中国有几十年的实地经验与研究。从我们共同撰写的几十个案例中不难发现,上述这些观点均有可取之处(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许多最具创新能力的西方公司也是由工程师创办的)。不过,这些批评无法揭示当代中国创新状况的全貌。中国不乏企业家和市场需求;而且基于中国政府的雄厚财力和强烈的政治意愿,中国完全有潜力制定出一系列经济政策,重构教育和科研机构。美国正是依靠这些措施成长为科技强国的。但这种潜力能否变为真实的能力?在我们看来,中国面临的挑战相当巨大。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收购式创新和基于教育改革的创新,纵观中国创新发展现状,人们可以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对中国寻求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前景和所面临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自上而下
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在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社会”,到2050年实现科技强国。这看似不是空话。中国中央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并制定了相应的监督措施,督促地方官员彻底贯彻这一国策,甚至村级官员也被纳入其中。
事实上,近4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动用财政资金,自上而下地刺激创新,并表露出强烈的政策意志。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并改革了苏联式的中国科学院,以便在同行评审(而非政治)基础上,为预商用的大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这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运作方式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国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资助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的进一步商业化。1985年,第一个高新开发区在深圳成立,此后这种趋势在中国势不可挡。如今,高新区已成为中国政府官员考察各大城市的常规项目。
对风电行业的鼓励政策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新兴创新产业的推动作用。2002年,为鼓励制造商的竞争,中国政府对风电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国外进口产品很快涌入尚未成熟的中国市场。仿照其他行业的模式,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在采购时,国内企业产品必须占70%。虽然外国公司持续在中国加大投资,但到2009年,在排名前10位的风电企业中,中资企业达6家。这促使国内企业的产品销量在全行业总销售额的占比呈井喷式增长,从2006年的51%一跃升至2010年的93%。
依据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在短短几年内,中国要实现对进口技术的依赖度降至30%以下,增加国内研发资金,在政府确定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即生物技术、节能技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和先进材料)领域,超越国外竞争对手。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给予中国公司出口补贴,并出台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尽可能采购本国公司产品。尽管有人指责这违背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的条款,但极少有跨国公司因此退出中国市场,相反,它们顺应了中国支持自主创新的进程。
中国政府常常设定宏大的目标,其实现目标的能力在高铁项目和登月计划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项国家级项目,需要投入的资金、技术和改良技术,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我们相信,在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治意愿下,中国能够像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那样,通过政府资助项目实现创新的目标。
自下而上
尽管中国强力推行创新国策,但即便是最强有力、最有信心的政府也难免力有不逮。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对于创新的阻碍作用绝不容忽视。
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探究这些是如何束缚企业创造力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留学美国的田溯宁返回中国,创办了亚信公司(即现在的亚信联创)。这家电信业的初创公司,三年内成长为320名员工、收入4500万美元的公司。
1996年,出于对中国电信业技术变革步伐缓慢的失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说服田溯宁离开亚信,去领导一家刚创立的新公司——中国网通。该公司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连接300座城市的光纤网络。2001年,当三位作者中的一人(麦克法兰)参观该公司时发现,这是一家极具创新性的公司,拥有开放的创意文化,尽管它的四个股东都是政府机构。
2002年,电信巨头中国电信被政府拆分,该公司在北方10省的分公司被划归中国网通旗下。一夜之间,田溯宁要负责管理一家拥有23万名员工的企业。
两个组织之间的文化冲突异常激烈。许多中国电信员工视田溯宁为来自美国的外来人,认为他要用不符合国情的方法改造公司。合并半年后,麦克法兰把我们所做的中国网通案例拿给70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看,其中包括20名电信从业人员。这些人非但没有从案例中组织变革和商业成功之间的关系中学有所得,反而集体攻击田溯宁,认为他的管理方式不够“中国化”,同时指责麦克法兰没有从积极的角度呈现中国背景下的硅谷文化。田溯宁很快辞去了中国网通的CEO职位,后来又退出了董事会。
由于要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中国网通最终外表看起来很像一家现代化的电信公司,但它的核心仍是国有企业。
但即使没有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市场的现实仍然促使企业追求渐进式发展而非突破性创新。想一想B2B门户阿里巴巴公司,这家网站在2001年摇摇欲坠,让人担心它随时会破产。但是,通过创造性地改进国外技术,满足发展中市场的需求,阿里巴巴目前在近250个国家为8000万客户提供服务,旗下的拍卖网站淘宝网最终成功将eBay挤出中国。百度的例子也很有趣,作为中国搜索引擎的领导企业,它既无任何技术突破,也不挑战政治权威,但在中国本土的成长极其迅速。为满足中国区域市场的不同需要,它量身定制产品,并进行组织和流程改造,如今百度占据着世界最大搜索市场80%份额。
二战后的30年间,日本很多行业在技术上超越了美国。现在,中国正在通过渐进式创新做着同样的事。技术改良已成为一种收益丰厚的惯用做法。不过,通过收购获得技术则是不可忽视的新趋势。
收购式创新
媒体已多次报道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热潮,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标的大部分集中在大宗商品和资源行业,投资地多集中在非洲与拉丁美洲。
但最近,中国企业开始加大对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投资,这一趋势不可小觑。其背后原因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厌倦向西方公司支付高额的许可费和专利费,在政府鼓励下,它们寻求通过收购技术和人才,达到购买而非租用突破性创新能力的目的。
华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公司驻华盛顿特区对外事务副总裁、美国前外交官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mer)曾将这家电信巨头形容为“你从未听说过的大公司”。当华为在全球设立了16家研发中心,并试图并购美国公司之后,现在没有人再这么形容华为了。(同时,华为在美国的并购也引来了诸多非议。)
海尔,中国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的领头制造商,同样拥有广泛的全球设计和研发中心网络,遍及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意大利都灵则成为中国汽车制造商的选择,江淮汽车、一汽、长安在当地设立了研发中心。
尽管国内的反西方文化潮流可能还很强劲,但在海外经营的中国民营企业已开始接受外国当地的高级人才。普卢默并不是惟一一位在华为工作的西方高级人才。2010年,该公司聘请了北电网络(Nortel)前首席技术官约翰·罗伊斯(John Roese),负责公司在北美的研发业务。
此前一年,英国电信首席技术官马特·布罗斯(Matt Bross)加盟华为,负责公司总共25亿美元的研发预算和运营。他们都直接向华为创始人兼董事长任正非汇报。同样,风机制造商金风科技(Goldwind)聘请了来自美国清洁能源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蒂姆·罗森茨维格(Tim Rosenzweig),担任公司负责美国业务运营的首任CEO。他又带来了几位拥有卓越背景的跨文化经历与行业专业知识的高级管理人才。
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的主要国际竞争对手包括卡特彼勒和小松。最初,三一曾试图依靠本土人才和技术在欧洲和美国取得成功。但几次失误促使企业在与欧洲和美国地区总部紧密相连的地点,建立研发中心,就地招募当地的专业人才。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著名水泥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从曾经的竞争对手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简言之,我们看到中国企业通过日益广泛的收购和合作,填补创新能力上的短板,它们步调一致且成绩斐然。
不过,要成为21世纪创新的领军力量,中国还需要培育未来的创新者。这是中国大学的责任。
教育创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就曾建立了强大的国立高校,如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与此同时,一批具有创造性的私立高校应运而生。
如今,中国的大学东山再起。以清华大学为例。该学校成立于1911年,原本是为期两年的文科大学,专为学生留学美国所设的预备学校,民国时期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到20世纪50年代,学校演变为苏联式的理工类大学。如今,这所学校重新回归为大型综合性大学,入学难度超过哈佛和耶鲁。2016年,清华将开设其首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学院——施瓦茨曼学院,以美国捐赠者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的名字命名,每年招收200名研究生,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清华大学相信,施瓦茨曼学院的学者将成为21世纪的罗德学者。(罗德奖学金是一个世界级的奖学金,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的美誉,得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译者注)。
就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而言,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战后扩张或20世纪70、80年代欧洲众多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近年来中国在中学后教育体系上的变化更为显著。文革十年大多数院校被关闭,1978年中国的大学向不到100万学生敞开大门。1998年,入学人数已达到340万,依然远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450万。而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已达2390万,比同年美国大学入学人数多400万。
如今,民办院校和大学在中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25%,与公立院校相比,它们的成长速度更快。大型公司也越来越多地涉足教育领域。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建立了淘宝大学,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电子商务经营者、管理者和销售人员。在未来,它将为超过100万在线学生提供商业教育。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每年将产生更多的博士生,其数量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大学正致力于打造高层次、创造性研究和人才的摇篮,将科研与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政府和很多机构都不惜重金资助中国的一流院校。在10年内,中国一些顶级大学的研究经费将追赶上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同行。而在工程和科学方面,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21世纪,中国的高校能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标杆?很有可能(尽管目前未有一所中国大学排名在全球前50名),原因很简单,它们拥有相应的资源。但关键问题是,中国高校能否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框架。目前我们的答案可能还是否定的。
在大学里,创新的先决条件是自由追求思想。但是,诸多可比指标显示,中国教学机构中的教师极少或根本无法在治理中发挥作用。
像绝对领导和绝对权力一样,绝对创新的意义也被高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业和教育都能享受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后发优势”,即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高。
当然,近十年来,中国通过技术改良确实实现了一些创新,展现出了一定的创新实力,并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中国能就此领先于全世界吗?中国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能接纳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的全面崛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存疑虑。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中国人的创新或知识能力无关,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拥有无穷的潜力,但与其基础教育、大学以及企业有关,在这些机构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限制。(译/陈晨 校/康欣叶 编辑/时青靖)
雷影娜是沃顿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劳德研究所(Lauder Institute)全球项目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资深讲师。
柯伟林是哈佛商学院斯潘格勒工商管理学科的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
沃伦·麦克法兰是哈佛商学院贝克基金教授及工商管理阿尔伯特·戈登教席荣誉退休教授。三人合著的《中国能否引领世界》(“Can China Lead? Reaching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Growth”)由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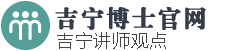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